心理导读: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人挑战精神科医生的权力、业务和自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传统的学术的和生物学精神病学遭到批评家们、持异议者和改革者们的尖锐攻击。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精神病学处在危机中,越来越少的医学院学生选择其作为自己的专科。 ---www.tsps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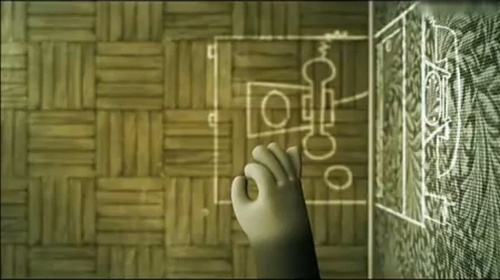
心理学堂: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
最近在一次长途飞行中,我观看了电影《飞越疯人院》。这部1975年制作的电影是根据一本同名的、写于1962年的书改编的。电影很经典,依然极富感染力。原书则是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高潮之际写的。1960年,萨斯[1]写作了《虚构的精神疾病》;1961年,高夫曼[2]写作了《精神病院》;1967年,库珀[3]写作了《精神病学与反精神病学》。我想:反精神病运动究竟怎么样了?
在很多国家,那些又大又气派的维多利亚式精神病院都关掉了。在消除关于精神病的污名和偏见上,人们做了很多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致力于增加公众的心理健康知识。
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人挑战精神科医生的权力、业务和自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传统的学术的和生物学精神病学[4]遭到批评家们、持异议者和改革者们的尖锐攻击。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精神病学处在危机中,越来越少的医学院学生选择其作为自己的专科。
艺术家、作家以及病人群体强烈反对各种“精神”疾病的具体治疗手段(药品、电击和手术)的描述一直以来都存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一些著名案例表明了:精神病学可以被用来当作政治压迫的一种武器。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精神科医生看来成了政府镇压武器的一部分。而确实地,拉多万·卡拉季奇[5],人称“波斯尼亚屠夫”的,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反精神病学的评论家们倾向于质疑以下三点:精神病的医学化倾向; 精神疾病存在与否的问题;精神科医生扣留和治疗某些人的权力。评论家们看到许多政府机构,特别是精神病院扭曲和压抑不同群体的人文精神和潜力。这些机构更像是监狱而非医院。
然而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才有人使用“反精神病学”一词。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反对既定的正统观念的激进看法出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聚集在“反精神病学”大旗下的各种群体内部又有一些不同的支流。可能出人意料的是,精神病学最重要的批评家是精神科医生们。
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6]
七十年代初有一个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反精神病学的研究。八名精神“正常”的、健康的研究人员试着通过诊断住进美国的几家精神病院。他们报告的唯一症状是听到某种声音(说点“空洞”之类的话)。其中的七个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让他们住了院。一旦入住,他们表现得很正常;当他们有礼貌地询问情况时,无人理睬他们。这七个人后来报告说:他们的诊断标签——精神分裂症意味着他们在精神病院里地位低、力量极小。
然后他们决定“和盘托出”,承认自己没有症状且感觉良好。但是他们花了近三个星期才得以出院,大多数人的出院诊断是“精神分裂症缓解中”。因此,正常的、健康的人如果欺骗医生说他们有人所共知的某些症状的话,可能会被轻易地诊断为不正常。
但是反过来,精神病人会被看作健康的人吗?同样的这些研究人员告诉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有伪装或冒充精神分裂的病人试图得到住院的机会。结果,他们发现:两名甚至更多名工作人员(包括一位精神科医生)怀疑19位真正的病人是装病!
结论是:在精神病院里,要区别神智健全的人与疯癫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儿。虽然这个著名的实验受到大量道德上的和实验上的批评,它给反精神病学运动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在整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这个实验依然是最著名的研究之一。
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历史
反精神病学运动有三个主要源头:
第一个源头始于五十年代早期,是弗洛伊德启发的精神分析派精神科医生与新的生物物理派精神科医生大战的结果。当时,前者正在失去其影响力,他们赞成长期的、动态的、谈话疗法, 遭到后者的挑战。后者认为前者的做法不仅昂贵、低效,而且非常不科学。生物派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手段是手术和药物治疗;他们在早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于是,老警卫挑战新警卫。当然,今天持续发展中的生物派精神病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为我们带来研究的突破,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更有效地治疗它们。
第二轮攻击始于六十年代,由著名人物如大卫·库珀,R.D]莱恩[7]和托马斯·萨斯等从不同的国家,对用精神病学控制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这一做法进行了高度的批判。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性、政治或道德上离经叛道或与众不同的人遭到了精神病学的审查与控制。那本名著《虚构的精神疾病》把他们的这一立场说明得很充分。莱恩成了一个偶像。我记得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会上听莱恩朗读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原创诗歌的情形。
第三股力量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学家们,著名的有厄文·高夫曼和米歇尔·福柯[8]。他们看到了精神病学有欺骗性的权力及其对被贴标签、被污名化和被住院的人们的影响。这些重要的社会学家们的影响力增长了;我们今天仍然能听到他们刺耳的批评。
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高潮是在六十年代的反文化、挑战一切的时代精神中。其时许多大众欢迎的电影、激进的杂志涌现出来,挑战生物学精神科医生、挑战政府设立的精神病服务及精神病学业务。
反精神病学运动一直是社会行动组织的一个松散的联合阵线。每个社会行动组织往往专注于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精神分裂症或者性功能障碍。他们讨论的是精神疾病的真实性和人的解放的问题,赋予病人权力和对疾病进行个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使用药物。他们还讨论了污名和歧视。许多人开始抨击制药工业。还有一些人对于社会权力和控制感兴趣。
基本理念
反精神病学运动有一些大家都认同的基本信念和担忧。第一点是:精神疾病的成因上,家庭、社会制度和政府与个人的生理功能或基因构造一样重要。第二点:他们反对精神疾病的医药模式和治疗手段。他们相信:那些依据与众不同的行为守则活着的人被错误地、危险地贴上了妄想的、危险的或有病的标签。第三点:他们相信,某些宗教和种族群体受到了压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是不正常的。这些群体被归为病态,被迫相信自己需要治疗,好治愈他们身上的疾病。
当年也好,现在也罢,反精神病学运动一直非常关注诊断标签的力量。他们认为那些标签给人一种虚假的准确和不变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精神病学运动成功了:现在人们通常不说“精神分裂者”而说“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不说“艾滋病受害者”而说“有艾滋病的人”。诊断标签和手册遭到排斥,因为许多人或者不符合任何诊断的标准,或者同时符合好多个诊断的标准;并且专家们对诊断的意见少有一致的。事实上,这一争论大部分是和用语有关,是担忧非常特别而重大的术语的使用对个人的影响。
对治疗手段的攻击
反精神病学运动还把矛头指向非常具体的治疗手段,特别是用药。在主要用来治疗儿童问题(多动症)和抑郁症的专门药物上面,反精神病学运动特别有意见。这些药物被抨击是因为其价格、其副作用,更是因为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病人没有被告知真相。反精神病学运动关注了制药公司举措的各个方面。他们认为:制药公司经常伪造数据,并且大规模地敲消费者的竹竿。这反过来导致制药工业被立法机关仔细监控和审查。今天,反精神病学运动依然坚持认为:制药工业对那些参与制定诊断机制(比如《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9] 第五版)的人有影响力;精神科医生被鼓励“去命名”那些看来只有非常特别的药物能够治愈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障碍。
反精神病学运动批评的其它靶子还有:电击疗法[10]、脑前额叶切除术[11]等特殊手术。尽管有某些成功的证据,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治疗手段是“强加”在单纯的病人身上的,并且会带来大量的、永久性的副作用。然而这些论争绝大部分已经结束了,因为如今这些手段都极少用到。
精神科医生强行隔离病人或强迫病人住院的权力也遭到了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抨击。很多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评论家认为: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是政府的一条臂膀;他们和警察、法官和陪审员的作用相同,只不过穿着白大褂而已。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也许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相对较少看到媒体提出这些问题。
反精神病学的倡导者总是呼吁更“人性化的精神病学”。他们曾经,如今也依然倾向于精神疾病的社会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精神分析的解释。他们依然在挑战精神病学的语言,以及一种妄想,即寻找生物学和基因学解释和治愈手段的生物医药的、科学的精神病学的妄想。因此,比如,他们也许会认为贫穷,而不是神经递质功能紊乱,才是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或者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成因中混乱和贫困的生活方式与大脑故障同样重要。
该运动最早期主要参与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相当政治化的反简化论者[12] 。他们试图为精神病学赶走邪魔、恢复本来面目。许多人反对“体制”;在很多方面来说他们胜利了。很多治疗方法停止使用了,很多精神病院关闭了。精神病学的标签已经改变了;精神科医生在使用这些标签的时候更为谨慎。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精神病学本体论也有了很大改观。精神科医生看上去也不具有他们曾经有过的权力和影响力。
反精神病学运动已经转化为基于病人的消费者运动。其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企图瓦解有组织的精神病学,而在于促进病人的权利和力量。
新精神病学
许多精神科医生试图通过遵循一些具体的原则或方针来回应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批评。因此,他们可能会尝试实行以下几条:第一,承认治疗的目标是好转,而不是仅仅增加洞察力或自我了解。第二,治疗手段应该是实证的,且只使用经过验证的治疗方法。第三,相信病人有权审阅其病历、了解其诊断、了解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各种治疗有何风险。病人和精神科医生应该对治疗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有现实的期望。所有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都值得关心、同情和尊重。最后,精神科医生不应该(他们也不够格)替病人做任何道德的、社会的或经济上的决定。
参考文献:
[1] 萨斯(Szasz)即下文的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1920年至2012年),著名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师。
[2] 高夫曼(Goffman),即下文的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22年-1982年),加拿大籍社会学家,活跃在美国学术界,曾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
[3] 库珀(Cooper),即下文的大卫.库珀(David Cooper, 1931年至1986年),是南非精神科医生和反精神病运动的理论家。
[4] 生物学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 or Biopsychiatry)是旨在从神经系统的生物学功能上来理解精神障碍的学科。
[5] 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i. ,生于1945年)是精神病学家,曾任塞族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2年-1996年)。由1995年开始,他被国际法庭战争罪行法庭通缉。法庭指控他涉及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2008年7月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不久被引渡至海牙受审。
[6] 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Being sane in an insane place)是化用了罗森汉[13]实验(the Rosenhan experiment)发表在1973年《科学》[14]杂志上的报告名《论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这一部分说的实验就是罗森汉实验。
[7] R.D 莱恩,全名罗纳德.大卫.莱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年 – 1989年)是苏格兰精神科医生,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重要人物。
[8]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9]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最新版——2013年出炉的第五版被简称为DSM-V)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是一本在美国与一些国家常用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
[10] 电击疗法(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简称ECT)是经由电击脑部的方式来诱发痉孪,以治疗精神疾患的方式;是精神科用来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物理治疗法,尤其当所有其它疗法都无效时,起源于三十年代。
[11] 脑前额叶切除术(prefrontal lobotomies)是一种神经外科手术,包括切除脑前额叶外皮的连接组织,主要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用来医治一些精神病,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精神外科手术。
[12] 反简化论者(anti-reductionists)就是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Reductionism)[15]的哲学思想。
[13] 罗森汉,即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1929年 – 2012年)是美国心理学家,以罗森汉实验闻名于世。
[14] 《科学》(Science)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
[15] 还原论或简化论(Reductionism)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
(译者/公子重牙 | 原作者/Adrian Furnham Ph.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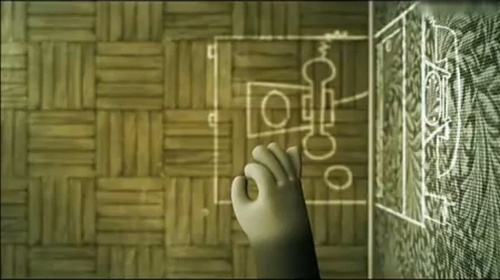
 女人做春梦的真相
女人做春梦的真相 心理学堂:母子乱伦的社会性思考
心理学堂:母子乱伦的社会性思考 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如何安慰?
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如何安慰? 心理揭秘:女人渴望被强奸?
心理揭秘:女人渴望被强奸? 为什么有人喜欢揭伤疤?
为什么有人喜欢揭伤疤? 心理揭秘:母子乱伦心理分析
心理揭秘:母子乱伦心理分析 心理学研究:黑暗三性格
心理学研究:黑暗三性格 社会热点:韩亚空难与权力距离指数
社会热点:韩亚空难与权力距离指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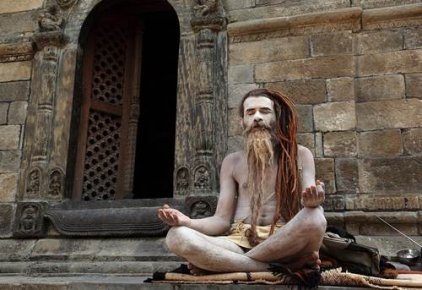 心理学堂:冥想能重塑大脑的结构
心理学堂:冥想能重塑大脑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