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卡尔·荣格是西方心理学巨擘,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1875-1961年)。而藏传佛教诞生在世界屋脊雪域高原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更有着近千年的差距,它们之间怎么对话?有必要对话吗?人们不禁要有疑惑。 ---www.tspsy.com
“我们必须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在我们的内心寻求它们……”
—— 卡尔·荣格
卡尔·荣格是西方心理学巨擘,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1875—1961年)。而藏传佛教诞生在世界屋脊雪域高原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更有着近千年的差距,它们之间怎么对话?有必要对话吗?人们不禁要有疑惑。
然而,美国的拉·莫阿卡宁却坚信在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这两种体系之间必定具有某种深刻、重要的联系。在他看来,藏传佛教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心理学和伦理体系,而藏传佛教密宗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过程,“它在我们深切向往象征性和精神的神秘性,及我们需求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始终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置身生活之中”。这么一来,就和卡尔·荣格一生致力研究的意识扩展和精神转化过程的论题便有了最直接的联系。于是莫阿卡宁“开始了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的令人激动的漫游”,并且在几年的漫游之后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本书——《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
在书中,他力图证明藏传佛教徒和卡尔·荣格各自从他们独特的方向,用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象征向我们一致表明:智慧是普遍的,排斥丰富的西方象征,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和损失。然而,东方的象征对西方人的心灵来说更为新奇,从而也具有更大的激发和刺激想象的能力。这在藏传佛教热浪冲击西方神学体系的今天,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时间、空间上的差异并没有损害藏传佛教和荣格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于是才会有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而西方世界的人们也能从这两种体系慷慨奉献的财富中各取所需,汲取无穷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你能说这种对话不值得吗?
在这里我们不想介绍太多的索然无味的名词、概念,力图以普通的语言来介绍两种体系的对话。一方是藏传佛教的朱古(活佛),一方是卡尔·荣格的徒子徒孙,旁白则非拉·莫阿卡宁莫属了。对话的主题则是关于痛苦和解脱痛苦的方法。我们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是世间众生最普遍关心的问题。
莫阿卡宁:对话一开始就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两者针锋相对,对痛苦是否能被超越发生了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真诚的交流。
朱古:并非罪恶,而是无明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佛教最关心的是消灭痛苦,因为它相信痛苦实际上是可以被超越的,摆脱痛苦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荣格:我完全赞同你所说的无明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按我的说法,这是因为自我认识的贫乏,使得人们被无意识的冲动所奴役。但痛苦是生活的本来状态,甚至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除的必要元素。人们必须面对痛苦的问题,痛苦又必须被克服,而克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忍受它。
朱古:藏传佛教认为痛苦是可以被转化为欢乐的。虽然说在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过程中绝不是没有痛苦,功德高深的修行者也可能要经受各种痛苦的考验,但其最终的结果必是极乐。
荣格:很遗憾,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痛苦和欢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组对立面,没有一方,另一方也就无法存在。为了保持生活的圆满和完整性,需要有欢乐和痛者之间的平衡。痛苦是自然的,不是生活中的病态;欢乐只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状态。
朱古: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重要。佛教所迫求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人类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想来在这方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荣格:一点不错,医治人类精神的创伤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工作。为此,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走出了一条精神疗法的路子。我的精神疗法不仅仅是对病症的治疗,更重要的是实现个体的完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切未来发展的种子,我的任务便是帮助这颗种子发展、成熟,直到发挥它的最佳潜能。
朱古:你的精神疗法和佛陀的体验如出一辙,佛陀用他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直接体验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赋予生命的价值。同时,也只有通过发展菩提觉,即绝对的、无限的、超自然的意识,在人自性中的亲证,我们每个人才能寻求到根本存在的问题的答案。
莫阿卡宁:换句说法就是,我们既没有必要到遥远的、神秘的地方去寻找它,也没必要从书本或者圣典中寻找它,只需在一个人自己的灵魂深处寻找它,也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它。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荣格:听其自然,这是最好的敲门砖。我仔细观察过那些成功地摆脱生活问题缠扰的患者,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简单地顺其自然,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允许自己的无意识在寂静中和他们交谈,他们耐心地倾听它的信息,并给予它们最大的和最认真的关注。这样创造出更广阔的人格、意识增强并发生转化,人的自性即灵魂显现。其实,在这个心理平静发展的过程中,无意识丰富了意识,意识又照亮了无意识,这两个对立面的融汇和结合,使认识增强,人格扩展。
朱古:对。一旦在个人的心灵深处认识到这种意识的转化,也就达到了佛教所常说的彻悟。
莫阿卡宁:两者所要极力证明的是一个同样的主题:人类的精神心理自身具有解脱的可能,即通过人内在的自我转化获得解脱,但它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自然发生,不能强制。基于同样的认识,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开始寻找解脱痛苦或者说救治灵魂的方法。
朱古:获得解脱的方法和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藏传佛教有着它独特的修行方式和技巧。它们是身(肉体)、口(言语)、意(心灵)三者完美的结合。
身指的是手结印契。印契是一些象征性的姿势和手势,手和每根手指都做出最优雅、美妙和意味深长的动作。藏传佛教密宗认为,它们是身体反映内心存在状态的外部表现,在适当的场合使用它,就有助于达到禅定,能够激发意识的更高层次。
口则指口诵真言。真言也称咒语,是一些神圣的声音,也是听觉符号。它们没有具体的含义,但像音乐和诗歌的声调和韵律一样,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探沉的情感和超越思想及日常语言的意识状态。对入门者来说,用一种非常直接、坦诚的方式背诵真言,就能唤起内心潜在的力量。但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正确的精神态度,只背咒语也无济于事。藏传佛教认为,真言必须从意念中产生,让心灵来倾听。
意则指心观佛尊。当人类生命的三个方面——身、口、意——同时存在并和谐地互相配合时,就会唤醒原始的宇宙力量,产生惊人的效果,人就能进入另一种实在。
荣格:说到这里,我想先打断你下面的论述。我对东方的宗教有一定的思考,我用以治疗灵魂的方法即和冥思修炼的基本方法相似。这尤其以积极想象法为最。积极想象的过程实质上包含两个对立面,即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不断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性各方面逐渐整合成为一体。对立双方的统一和融合作用最终导致心理转化。
这一过程分几个阶段。最初是诱导出宁静的心灵状态,摆脱一切思绪,不作任何判断,用自然的方法观察,注视着无意识内容和支离破碎的幻想片段自发地出现、展开,然后用书面形式及其他有形的图形,如画、图、雕塑、舞蹈或其他任何象征表现手法,把这种体验记录下来。在下一个阶段,心灵的意识开始积极地蓄意参与和无意识的对峙,无意识产物的意义及其信息被理解,并且与心灵的意识状态和谐一致。
确切地说,它好像两个有同等权利的人之间的对话。他们都相信对方的论证正确,认为值得通过比较和讨论来修改互相矛盾的观点,否则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
最后,一旦自我和无意识相互妥协,个人能够有意识地生活,就必须遵守某种伦理观点和义务:即个人再不能像以前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潜在作用时那样看待他的生活。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很清楚?
莫阿卡宁:荣格积极想象这样的精神疗法旨在使他的病人心中造成一种流动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体验到不依附任何一成不变的条件变化和生长。同时,荣格努力在他的患者中间引发一种超越个人联系的感觉,以扩大他们的知觉能力,挣脱个人的意识,这对于理性观点受挫败和压抑了生命的精神领域的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
朱古:这种精神疗法的相似性恰好体现在心观佛尊之中。在身、口、意三者之间,它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禅定,用非专业化的语言来说是这样的:作为初步的实践,开始是以各种各样的冥思方法修炼,抑制心灵,使它平静、专注一心,培养注意力和知觉。在这一基础上再辅以更复杂的方法修炼。心观过程中,坐禅者在心中构想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精神意象,代表宁静、美丽、忿怒、恐怖的密宗神抵。众神和他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指引他们完成这一过程。
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和精神能力,禅定者被赋予不同的神,按照指令,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在心中创造的神的意象, 必须想象出神的形象的每个细节,它的整体状态和颜色,直到它变得和修行者一样真实。他们不仅在心中构想神,而且也把自己看作神。就在刹那间,他们化神为神,神的原型已转移到他们心中。这种心观的核心便在于人和神的统一。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坐禅者的自我和他们的一般意识被抛弃,被更高的神的意识所取代。仲巴仁波且在《密宗的起源》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冥想大日如来佛的景象:
在一轮皎洁明亮的秋月上,你放上一颗很小的芥子,芥子的凉爽的蓝光放射出无限清冷的怜悯,超越空间的限制,它满足了有情众生的需要和愿望,送来必需的温暖,澄清混乱。然后从这颗芥子中,你创造出白色、具有贵相的大日如来佛——一个8岁的孩童,用美丽、天真、纯洁、有力、高贵的目光凝视着你。他身着中世纪印度国王的服饰:头戴闪闪发光、镶嵌着满足希望的宝石金冠。他长长的黑发一部分飘动在肩和背上,其余的梳成顶髻,佩戴着一颖闪闪发亮的蓝色钻石。他盘腿坐在月盘上,双手呈禅定的手印,握着一枝白色水晶雕刻成的金刚杵。
您与大日如来佛融为一体。这时候,难道您不会显得安详、宁静吗?
荣格: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随着持之以恒的实践,作为意识发展的更高层次,心灵所创造的众神呈现为一种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坐禅者的生机勃勃的实体。而“心灵所创造的众神”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幻觉。
莫阿卡宁:荣格对幻觉下了这样的定义: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某种东西是幻觉?我们有权利把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任何东西称为幻觉吗?我们愿意称为幻觉的东西可能是对心灵极其重要的生命要素,就像氧气对于身体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一种极具重要意义的心灵的实在性。心灵大概不会为我们的实体范畴而烦恼,对它而言,任何起作用的事物都是真实的……也许,对心灵来说,再没有任何事物比我们称之为幻觉的东西更真实了。
莫阿卡宁:荣格和藏传佛教的朱古两人在解脱痛苦的方法上实质都强调了直观的重要性。但前者强调的是一种通向隐藏着彻悟和自性种子的内在核心的动态方法,后者强调的则是一种非教条的旨在获得活生生的内心体验的经验方法。
莫阿卡宁:寻求解脱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精神上的向导,痛苦还是难以解脱的。担当起拯救灵魂、解脱痛苦的人,在荣格称之为治疗学家,在藏传佛教则称上师(即朱古)。他们同样起着精神向导的作用,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荣格:治疗学家至关重要之处在于精神治疗的作用和他与患者的密切关系。治疗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种精神实体互相对峙,二者在冲突中必然会互相影响、转化。因此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学家必然会受到接受治疗者的影响。对于治疗学家来说,一方面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复活的体验,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患者心灵的污染,威胁着治疗学家自身情绪的平衡。这应该说是难免的。
朱古:从这一点上说,上师要比心理治疗学家更完善。藏传佛教对上师的资格要求很严,他必须具有高深的功德、明澈的心灵,是弟子获得彻悟的榜样!已经获得高度的精神彻悟的上师不可能受到心灵的污染,更不用说受弟子的消极影响了。
同时,藏传佛教并不把上师视为最终的权威。藏传佛教鼓励他的信徒以自己的经验来检验教义的正确性,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接受它,也就是说信徒个人特性的需求应摆在第一位。佛陀就曾因弟子的各自特点,用不同的语言向不同的人传授同样的真理。
荣格:您说得很对。个性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患者应在心理上日益成熟,依靠自己。就像炼丹术士的门徒,必须学习试验室的一切技巧一样,最终必须由自己来从事实验,因为这是别人无法替他们办到的。也就是说,只有个人的精神或心灵不受干扰时,才有客观地发挥作用的能力,从而把个体引向他的自性。
莫阿卡宁:我们不难看出,两者都强调解脱痛苦必须有人指导,但他们同样强调个人特定的需求、条件和能力。指出“修行者”最终必须摆脱任何权威的影响,把自己的心灵作为向导,在自己的心中发现真理,这才是解脱痛苦、治疗灵魂的必要条件和正确而唯一的途径。
解脱痛苦,是最受现代世界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东方的藏传佛教和西方的心理学家荣格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疗法。你何去何从?是心又致沸尊呢?还是积极想象?也许你两者都需要!因为这才能够解释西方世界的众生日益关注藏传佛教的现象。坐禅去,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口头禅。而原本流淌着白种人血液的西方人对荣格则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既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但更多的是对两者的融合,以创造出一个新天地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节选自《佛光西渐》黄维忠著 | 来源/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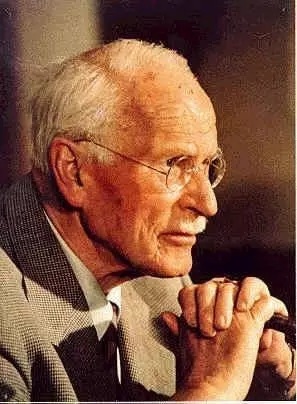
 心理沙盘:沙具的象征意义
心理沙盘:沙具的象征意义 沙盘游戏治疗:亭子的象征意义
沙盘游戏治疗:亭子的象征意义 沙盘中的水象征什么?
沙盘中的水象征什么? 沙盘游戏治疗:厄喀德那的神话传说
沙盘游戏治疗:厄喀德那的神话传说 沙盘游戏:建筑物的象征意义
沙盘游戏:建筑物的象征意义 沙盘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治疗案例
沙盘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治疗案例 沙盘治疗:大象在佛教中的象征意义
沙盘治疗:大象在佛教中的象征意义 沙盘疗法:如何对沙画进行主题分析?
沙盘疗法:如何对沙画进行主题分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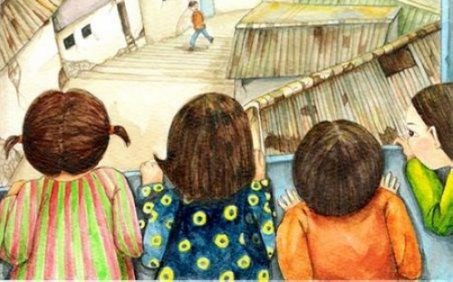 心理沙盘:沙盘游戏中事物的象征性
心理沙盘:沙盘游戏中事物的象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