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责任编辑:tspsy-张茵 发布于2024-03-17 11:30 浏览次
直面死亡有时候难以启齿
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有部分资源来自网络,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进行处理。
相关人气资讯 :
-
 兄妹乱伦不可承受的伤害
兄妹乱伦不可承受的伤害
心理导读:性侵害在任何社会背景下的任何时期都会发生,且形式多种多样。它给受害者造成深深的伤害,有的甚至是终身的,如何应对性侵害显得尤其重要。 ---心灵花园 兄妹之... -
 心理疾病:为何有些女人喜欢性虐待?
心理疾病:为何有些女人喜欢性虐待?
心理导读:牛郎店,众所周知是女性买春的地方。在牛郎店里,有些常客喜欢对牛郎进行性施虐,上演SM戏码。可怜的牛郎被打被骂不还手不还口,面对尖锐的高跟鞋还要强忍。为什... -
 “冰恋”:精神疾病性的SM
“冰恋”:精神疾病性的SM
心理导读:马尼奥塔事件发生后,国内部分性学家与网友认为其行为疑似冰恋,即SM(虐恋)中的最高层次:死亡调教。接下来我们以冰恋作为新知与大家一起来了解,消除大家对这... -
 捡垃圾成瘾:心理疾病惹的祸
捡垃圾成瘾:心理疾病惹的祸
心理导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老人拾荒,拾的正是心荒。用囤积废品,来获得相对的安全感;通过捡拾垃圾的过程释放自己的情感,充实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将自己的情感附于捡... -
 心理疾病:同性恋与恋足癖
心理疾病:同性恋与恋足癖
心理导读:恋足癖属于性倒错中的其中一种恋物癖。性倒错是一种性行为形态,需要藉着不寻常的物体,仪式或情境,才能得到完全的性满足。有些性倒错比较严重的个体,每天需要... -
 换偶群p拍裸照背后的心理动机
换偶群p拍裸照背后的心理动机
心理导读:近日,夫妻群P聚会成为讨论的热点。我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人类有寻求性爱刺激的需求,于是,一个著名的理论浮出水平,那便是柯立芝效应。 ---www.tspsy.com 换偶... -
 恋足癖与性冷淡,抑郁症,性厌恶
恋足癖与性冷淡,抑郁症,性厌恶
心理导读:恋足癖属于性倒错中的其中一种恋物癖。性倒错是一种性行为形态,需要藉着不寻常的物体,仪式或情境,才能得到完全的性满足。有些性倒错比较严重的个体,每天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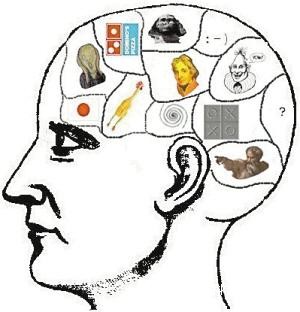 为什么精神病人爱裸奔?
为什么精神病人爱裸奔?
心理导读;另外一件发生在加拿大的疑似精神病食人事件,在一辆公交车上,一名乘客突然砍掉另一名乘客的脑袋,据传闻他之后就开始吃受害者。事后据袭击者称,他听到了上帝的... -
 心理疾病:如何治疗飞蚊症?
心理疾病:如何治疗飞蚊症?
心理导读:大部分飞蚊症患者会避免手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飞蚊症根除。然而,我们眼睛的自愈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www.tspsy.com 心理疾病:如何治疗...
电话:15232608868
微信:joelychou
Q Q:1374550583
Q Q:2363639583
Emall:tangshan@tspsy.com
地址:唐山站前路188号金凯悦商务中心A612
-
兄妹乱伦不可承受的伤害
浏览14545 次 -
心理疾病:为何有些女人喜欢性虐待?
浏览9230 次 -
“冰恋”:精神疾病性的SM
浏览5765 次 -
捡垃圾成瘾:心理疾病惹的祸
浏览4424 次 -
心理疾病:同性恋与恋足癖
浏览3690 次

-
【案例分析】母子乱伦背后的心路历程 79026 人浏览过
-
·人的潜意识是万能的吗? 353 人
·强迫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465 人
·灵魂伴侣是一个伪命题 665 人
·做心理咨询有风险吗? 667 人
·成长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531 人
·男人下班躲车里不回家 573 人
-
女儿想和我发生性关系 133851 人浏览过
-
·临终关怀-让生命温暖谢幕 139 人
·安娜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 110 人
·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怎么处罚 156 人
·心理学堂:文化偏见是怎样形成的 174 人
·心理学堂:从众是如何产生的? 134 人
·让大脑高效运作的方法 194 人


